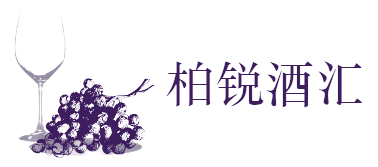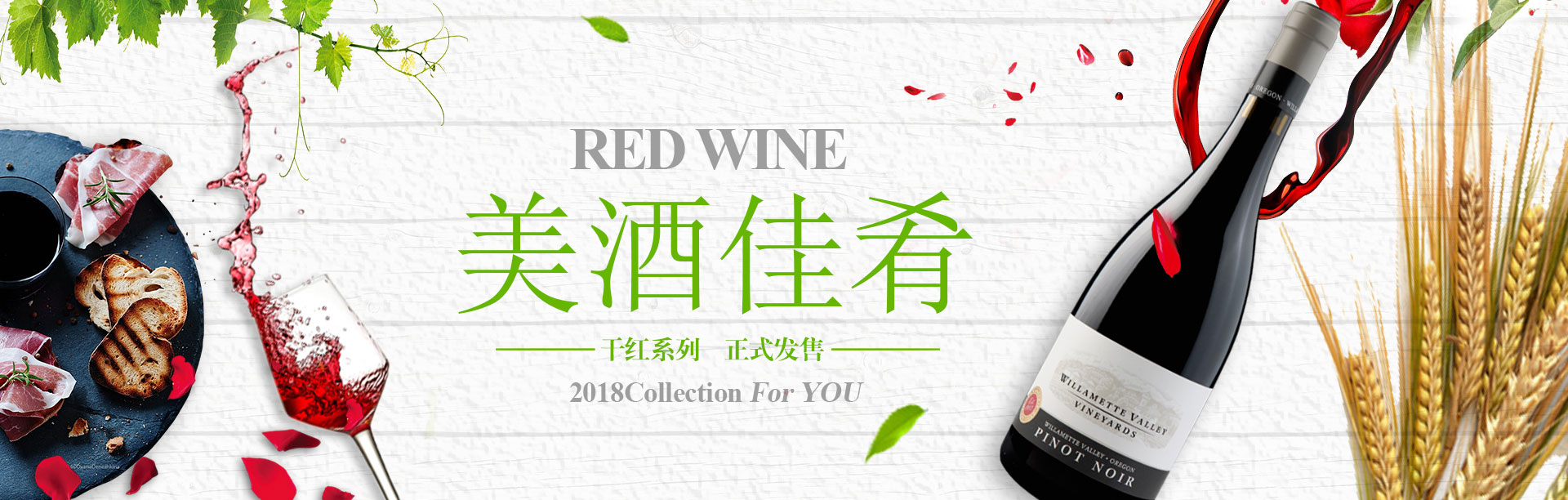诞生于中近东的葡萄酒先是传入埃及,经过希腊,向西扩展至欧洲,但它并没有进入东方。暂且将教禁酒这样的宗教、文化壁垒排开,印度、西亚、中国、以及更东的日本等国,也是葡萄酒的不毛之地。中国虽然自汉朝起,就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带来了葡萄,到唐朝时,文人墨客也开始喝到葡萄酒,并栽植葡萄,但在此之后,葡萄酒却忽然消失了。大洋彼岸的南北美洲也一直没有葡萄酒的身影。南北美洲开始酿造葡萄酒要到西班牙征服之后,由传教士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葡萄酒文化也没有在这些地区诞生,这并不是由于亚洲像中国人、日本人等地区的人们不喝酒造成的。
在日本,酿造以米作为原料的清酒时,为了产生酿酒所需的微生菌,使用了醪糟和酵母,它的酿造技术和工艺在世界上也属唯一。而世界各地也有椰子酒等用果实酿造的独特且种类繁多的酒,人们亦享受着他们带来的乐趣。从葡萄酒发展分布图就可知,埃及、犹太、希腊、罗马等文明在形成欧洲文化底色的“两希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的同时,作为其中一环葡萄酒文化也逐渐发育起来。
那么,葡萄酒是如何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起源,并在埃及、希腊、罗马、欧洲、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旧约与新约中对葡萄酒的描述有何不同?葡萄酒如何在罗马形成了平民化与贵族化的差异?葡萄酒在欧洲中世纪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又如何?本书对葡萄酒的历史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和影响做了详尽的叙述。
作者山本博,日本葡萄酒评论家,律师,出生于1931年。早稻田大学毕业。日本葡萄酒批评的先驱。葡萄酒相关作品超过40本。
译者瞿亮,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世界史博士,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在《世界历史》《历史教学》《外国问题研究》《世界历史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译有《安南史研究Ⅰ》《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天下泰平的江户时代》《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东南亚多文明世界的发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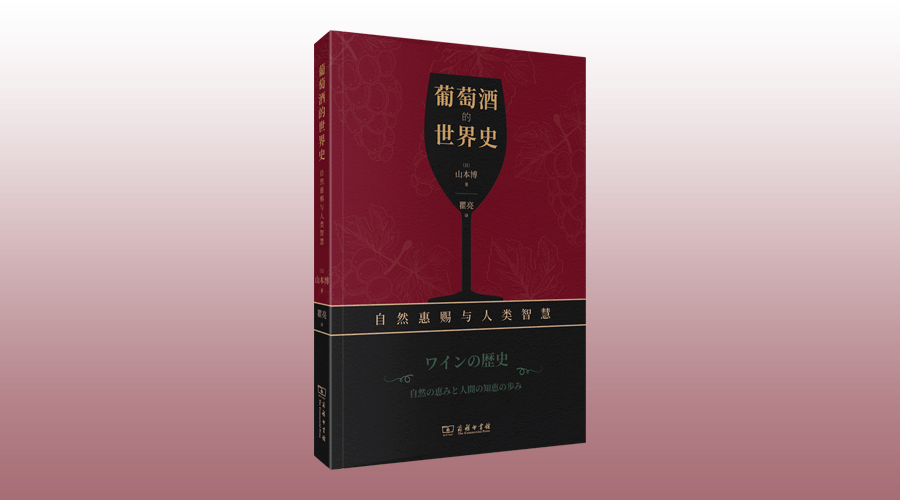
葡萄酒之所以被说成是一种文化,并非因为它是十分甘醇的饮品,而是因为喝葡萄酒显得时尚和华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认为,相比土气的威士忌和金酒,葡萄酒显得更具品位,因而倾向于饮用葡萄酒,使之得以逐渐流行开来,其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葡萄酒是人类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随着包括经济、社会在内所有周边条件的发展,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葡萄酒。最有力的说明例子便是猿酒。
猿酒传说是东洋所特有的,西欧则看不到,其根源来自中国。现代中国关于葡萄酒的释义书中亦记载了其起源。通过查阅得知,这多半是出自清代浮槎散人《秋坪新语》和寄泉《蜨阶外史》。唐代李肇《国史补》中,记载了为捕获名为猩猩的想象动物就令它喝酒醉倒,然而这并不是通常所谓的猿酒故事。根据浮槎散人的记述,在四川省边境靠近西藏门户的忠州地区山林中寄居了许多黑猿,相传它们擅长酿造好酒,村民们将佳肴、水果放到黑猿居住地附近,并在旁边放置空壶,黑猿发现佳肴(鱼、肉、水果)并争食,也把空壶带回洞窟装满了酒再放回原来放佳肴处,村民们趁机惊动并驱赶它们便可获得美酒。
而根据寄泉的记载,云南省靠近缅甸的永平县也有许多猿猴,人们趁大多猿猴成群迁徙之际,惊动其逃散,从而获得大量放置的陶器。开云网址陶器成土字型,是铸烧成型的成品。其内部盛满了清澈的汁液,汁液呈深红或浅绿色,酸甜涩兼具,十分芳醇。而这是猿猴采集山中水果酿造的,据说它们囤蓄食物过冬,在风雪天气无法去寻觅猎物的时候就饮用这陶器里的酒。
对当时居住在首都北京的文化人而言,由于交通手段有限,四川省、云南省是他们难以到达的偏僻之地,故只能从他人传说中了解情况。从那些地方到北京的人,被视为远道而来的客人而受到欢迎,他们说的虚构故事被信以为真,因此还留存了鬼首之类的记载。这样说来,日本也有着“取瘤子的老爷爷”这种属于无稽之谈的民间传说。而它也被江户时代日本的知识分子认为是确凿可信的。在今天的日本,要是相当有名的学者还相信这个故事,那就要闹大笑话了。
第一,原本猿猴并没有贮藏食物的行动意识。猿猴是哺乳动物中的灵长类,虽然他们具有类似于人类的智能,也有像松鼠这类动物一样储备过冬食物的习性,但它们无论如何也不会保存、蓄藏食物。《庄子》里狙公(饲养猿猴者)“朝三暮四”的故事,就形象地点明了猿猴的生存实态。在日本,猿猴虽然将生息的范围扩大到青森县积雪地区,它们甚至知道将薯类浸渍到海水中令其更具风味,但其习性也并未改变。
第二,虽然猿猴与贮藏有一些关联,但它们并不会制作陶器。退一步说,它们肯定不会使用火,即便它们做成了陶器泥土原胚,由于没有用火烧制的技术,就无法贮藏水和其他液体。虽然可以想象它们盗取人类制作的陶器,但这已超过了猿类的行动意识。人类自远古时代起,就开始考虑是否能够运送水和其他液体。他们想到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用葫芦。通过使用葫芦,人类可以离开水源地而生活,扩大了他们的行动圈。这也致使人类离开海洋而移住到远地成为可能。但猿猴不仅不会使用葫芦,而且它们也没有想要使用葫芦的意识。
倘若如后所述,假使一粒粒野生的葡萄掉落到木洞中积累起来,也无法酿造成葡萄酒。野生葡萄果梗强韧,即便是遭受到撕咬也很难摘下来,果房和果粒就更不可能从树上掉下来并积蓄起来。既然猿猴无法酿葡萄酒的话,那么古代日本人的酿酒情况如何呢?
古代中国留存了观察日本人的一系列史书(鸟越宪三郎《中国正史倭人·倭国传全译》),在《后汉书·东夷列传·倭》中有“人性嗜酒”的诠释,而后也出现了同样的文字记载。而在《魏志·倭人传》中,亦有“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的记载,与而今通宵守夜进行佛式“精进落”斋食相通。但日本人祖先所饮的也并非葡萄酒。
那史前时代的情况如何呢?持有如此兴趣的《周刊朝日》编辑岩田一平就著有《绳文人也喝酒啊》一书。除此之外,还有近年来围绕多处遗迹发掘的报告。绳文人喝葡萄酒这一通说的形成,是因为长野县井户尻遗迹挖掘出有孔锷陶器。该陶器的顶部有像锷一样的锐利之处,接续的尾部则有孔穴。有记载称“这种陶罐是用来处理山葡萄酿造果实酒的,其中的孔是为了解开缠绕蔓藤而特意烧制的”。
陶器底部还发现了山葡萄种子,发掘者虽然向媒体透露了这个推论,但“孤掌难鸣”。经过知名学者的公开发表,它才成为一种通说。(加藤百一《日本酒的500年》)
此后,各地都相继发掘了有孔锷陶器(尖石遗迹、开云网址井户尻遗迹、释迦堂遗迹等)。它们不仅数量繁多,类型也有大到近一米的大陶和小至巴掌般的小陶。虽然见到如此多数的形态,但是用这些特殊陶器来酿出发酵用的果汁,也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如后所述,浅井昭吾报告指出,虽然对各陶器进行了查验,但并未发现发酵产生的色素痕迹。
青森县的“三内丸山遗迹”是山葡萄系葡萄酒另一个有力的证据。这暗示了该地栽培了栗子树,其文化发展程度较高。1993年,从绳文时代前期的废弃考古场地中发现了厚度约达10厘米的种子层。在这些种子中包含了山葡萄,因而就有了该地酿造葡萄酒的传说。
该地发现了这些种子共同发酵产生的具有繁殖性的曲霉(《三内丸山遗迹与北部绳文世界》原文,但曲霉出现也十分微妙,曲霉是米的淀粉转化为糖分的时候产生的,而果汁糖分转化为酒精则并不需要曲霉),还发现了采集葡萄酒发酵果汁的猩猩果蝇化石。而无论是秋田县池内遗迹还是三内丸山遗迹,都发现了同样组织的植物化石块,由于其中包含了细小的纤维,因而推断其是榨取汁液后留下的渣滓。
看到如此的报告之后,就无法否定日本古代先民曾经酿造出了果实酒。然而,要想飞跃性地得出曾经酿造出葡萄酒的结论,就不得不倾听其他的研究。
实际上,该土层的种子群中包含了山葡萄、桑、猿梨、木莓、楮,而且这些并不唯该地仅有,在其他地区也有大量接骨木的种子(与本州各地所见的接骨木相异,是果粒更大的西伯利亚接骨木)。而且,在千叶市神门遗迹还挖掘发现了接骨木、木莓、桑、猿梨等。大津市粟津湖底的绳文时代中期遗迹中亦有接骨木、木莓、桑、猿梨等, 而且金泽市米原的绳文时代晚期遗迹中,与桑、接骨木、木莓一同发掘出来的还有各类山葡萄的种子。将它们发酵酿造的话,大概能够制成果实酒、药酒,但这也并非葡萄酒。
山葡萄酿造葡萄酒有几个难点。葡萄酒是由葡萄发酵酿造而成的,它需要适合葡萄栽培和发酵的气候,在类似地中海沿岸的地区酿造起来就相对简单,或看起来更加可行。然而,用葡萄酿成葡萄酒还需要历经几个鲜有揭露但又不可或缺的流程。首先是“发酵组织”的问题,葡萄果汁要成为葡萄酒,需要果汁中糖分附着于果皮等处,在酒酵母的作用之下,分解为酒精和碳酸气。酒酵母与其他多种野生酵母相互竞争维系发酵作用,虽然可制成酒精,但最初其他野生酵母的数量占优势。而随着发酵的进行,酒酵母逐渐增多,酒精含量亦增高,而没有如此韧劲的野生酵母就消亡了。
但是,要达到如此状况,就必须有协助酒酵母发育的充足的糖浓度。也就是说,果汁中若没有富含足够糖分,酒酵母的主要作用就发挥不出来,这会导致它们在与野生酵母的交锋中败下阵来而无法生成葡萄酒,果汁最终腐臭变质。在日本这样气候多湿的国家,水果的糖度很低,而野生的微生物则具有多繁殖多成长的强烈倾向。因此,没有达到足够充分的条件,仅放任不管的话,山葡萄转化为葡萄酒的现象很难发生。
“榨汁”也成了另一个大问题。有人在谈及普通山葡萄酿造葡萄酒的经验时,指出这出乎意料的困难。从葡萄的果粒变成果汁看似简单,但并非如此。仅将果粒捣碎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有“榨取”作业。葡萄果粒柔软滑溜不易抓取,仅用手挤榨只能获取少量果汁。
野生葡萄果粒被充分捣碎,发酵后压榨起来就会变得简易。因此就形成了先是简单地将果粒捣碎并发酵,其后再压榨的方法。如后所述,人类进行如此过程十分辛劳。况且,日本的山葡萄果粒小,含有的水分也不多。
古代人若有酿造果实酒的想法(到底是否有此想法尚具疑问),即便不用山葡萄,使用猿梨或者野生桑葚来酿造也更为容易。而今,我们已经将葡萄酒视为寻常之物,但仅仅知道它是由葡萄酿造而成,因此简单地将山葡萄与葡萄酒关联起来,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个大陷阱。若只是想榨取果汁,则可以采用其他果实。
古代日本人对于山葡萄的关注更聚焦在它的颜色上。山葡萄的其中一种,桑叶葡萄可用作染料,故日语保留了“虾染”这一词语。因此,有必要转变之前见到山葡萄就把它与制成饮料联系起来的想法。人类在山野中其实并没有食用大量葡萄,基于这种考虑,于是就形成了将它们干燥起来保存和设法将它们变为饮料的两种方法。在日本,有晒干柿子以确保过冬食物这样的劳作。相比酿酒,古代日本人考虑更多的是设法将其变成可以长久保存的食品。
世界上多数葡萄生产国中,不酿造葡萄酒而制成葡萄干的国家也不在少数。葡萄干制作方法简易,甜味十足,易于保存。而且在古代,人们酿造葡萄酒必须当即喝完。要保存、贮藏葡萄酒,需要更为高度精细的管理和文化。与美索不达米亚、希腊不同,中国西域丝绸之路沿线的诸国,皆没有酿造葡萄酒而是制作葡萄干。现在依然如此。如果将猿猴贮藏智慧视为其本能的话,相比酿造葡萄酒必须要使用工具而言(猿猴并不能使用工具),它们制作葡萄干则更合情合理。虽然属于虚构设想,但基于实际而撰的《鲁滨孙漂流记》中就谈到人们见到野生葡萄并没想到酿造葡萄酒而是制作葡萄干。
令该设想(进一步说是文化)受到关注的是浅井昭吾。他在莫西亚公司负责栽培葡萄期间,赌上自己人生,酿造了多种葡萄酒,因而被视为教父并受到尊敬。
浅井在留下的多部与葡萄酒相关的著述中,对古代日本人酿造葡萄酒的问题都进行了否定。将葡萄酿造成葡萄酒,只有在很难获得良好水源的干燥地带的人们才能这么去做。(作者在这方面其实很早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像日本这样稍微走一段路即可见到清冽水流的国家,根本不会诞生从如此小的果粒中大费周折获得饮料的想法。大概可以推断,居住在三内丸山地区的绳文人,见到山野中茂密的接骨木(其果实鲜红美丽),摘取它们当作染料的原料或用它们作为药用的原料,而不会产生而今我们印象中把它们用于酿造葡萄酒的想法。